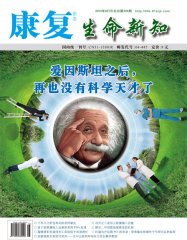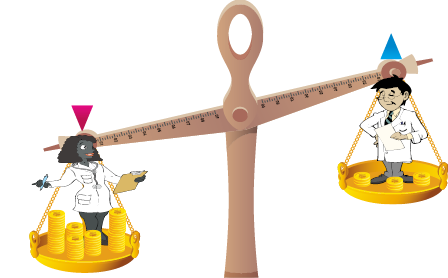白春学简介
1951年4月生,吉林人。教授,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呼吸内科主任,上海市呼吸病研究所和复旦大学呼吸病研究所所长,博士及博士后导师,中山医院肺部肿瘤综合诊疗中心主任。1982年获北京中国协和医科大学硕士学位,1989年获上海医科大学博士学位,1985年在日本进修结核病防治,1997年~1998年在美国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UCSF)心血管研究所做博士后研究。
上海市领军人才和上海市医学领军人才,兼任中华医学会呼吸分会副主任委员、上海医学会肺科学会前主任委员、亚太呼吸学会科研委员会主席、美国胸科医师学院(ACCP)中国负责人。Springer出版社《Translational Respiratory Medicine》主编、中国《国际呼吸杂志》和《呼吸新视野》杂志主编,英国《Journal of Clinical Bioinformatics》、英国《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美国《Journal of Epithelial Biology & Pharmacology》、《中华结核和呼吸杂志》、《中国实用内科杂志》、《中华肺病杂志》、《临床肺科》和《世界感染杂志》副主编,以及《American Journal of Respiratory and Critical Care Medicine(IF 11.8)》、《American Journal of Respiratory Cell and Molecular Biology(IF 5.15)》和《CHEST(IF 5.25)》等多家杂志编委。
从事呼吸内科和呼吸危重医学,主要研究方向为肺损伤和肺癌的分子发病机制和治疗。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等41项科研课题,发表论著420余篇,其中英文110篇,SCI论文影响因子累计430余分。主编《呼吸系统疾病诊断和鉴别诊断学》、《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呼吸病诊治纲要和质控要求》和《呼吸系统疾病的核医学检查》,参编多部专著和教科书。获得专利27项。
崇尚接轨国际的学术精神,提出“国际大会有声音、国际杂志有影响、国际学会有位置、国际社会有认可”的四有教授标准。倡导大爱无疆的职业精神,创立“接轨国际、面向世界、服务病人、造福社会”学科目标。在国际上最早提出基于手机的无线传感肺功能(专利号:ZL2009 2 0078022.4)并成功研究出样机,2009年ATS会刊(Who’s Who at ATS |ATS NEWS | VOL.35 NO.7/8,http:/ /www. thoracic. org)名人录为此刊登了专题报道,在此基础上提出基于手机的云加端物联网医学,建立世界首个睡眠呼吸暂停物联网医学家庭监护和管理平台。首创可实时监测血液pH、PO2和PCO2的荧光传感器,并发展出样机。在国内于2002年1月28日建立了首家肺部肿瘤综合诊疗中心,2007年建立首个飞机旅行和高原旅游健康门诊。
先后获2012年中国医师协会医师控烟领导力奖,2011年复旦大学校长奖;2009年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呼吸衰竭的发病机理与治疗研究”(第2完成人);2006年中华医学一等奖:“呼吸支持技术临床应用研究”(第3完成人); 2005和2009年分别获得上海市优秀发明选拔赛一等奖和金奖(第1完成人);以及“国家医药卫生科技进步三等奖”两次和其他多项奖励。
7月的一个午后,笔者在上海中山医院白春学教授的办公室见到了这位浑身散发着儒雅气质的呼吸专家。作为上海市“重中之重”临床学科——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呼吸内科的负责人、主任,他带领学科走上了发展快通道,使之成为拥有一个接轨国际的医师团队、两个创新实验室和三大接轨国际平台的国际化科室。繁忙的临床工作没有阻碍他创新的脚步,反而为他提供了灵感,光他自己的专利就达到了令人咂舌的27项之多,不得不说他在临床和科研创作间找到了完美的平衡。下面就让我们通过对话来了解他。
#p#副标题#e#
追逐名医的脚步
记:您之所以走上从医道路是受什么影响?
白:主要是受家庭影响。我外祖父是我们当地有名的中医,从小我母亲就熏陶我:医生门前过,必得让个座。意思就是医生是很有用处的,是治病救人的,在哪里都是受尊敬的。
记:您硕士是在协和读的,博士怎么会换到上海医科大学(简称上医)读呢?
白:我读研究生的时候比较早,1979年就考到北京协和医院读研究生,我们毕业的时候还没有分博士、硕士研究生,当时只有研究生,没有硕士、博士学位的区别,毕业后一年才给我们硕士学位。1986年时只有上医招呼吸专业的博士,所以我就考了上医的博士。而且我很向往名医、名导师。我在北京协和医院读研究生时的导师是朱贵卿教授,他在北方的呼吸界是最权威的,大家都非常认可他。中山医院这里是中国最早、历史最悠久的呼吸科,当时叫肺科。恰好也只有中山医院在招博士,我就考到这里了。如果用现在“追星族”这个词来形容的话,我就是名医的追星族。
留学开启事业新旅程
记:1997年,您46岁的时候怎么会想要出国学习?
白:其实早在1985年,受世界卫生组织支持,我曾经去日本留学半年。当时虽然日本的医学比中国发达,但在我看来还不是最发达的,美国是当时世界上医学最发达的国家,所以我有意到美国去进修、学习。事实上,在我博士刚毕业的时候,也联系过一些美国的大学,有些也给了我反馈,比如密西西比大学,但我觉得这个大学不是最有名的,而我想联系到最有名的大学去做博士后。1997年,在我46岁的时候,美国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Francisco,UCSF)有一个适合我的博士后位置,恰好导师也是世界上比较有名的、肺损伤的权威之一——Michael Matthay。他主要从事肺损伤的临床和研究工作,在世界同行中影响很大,很受认可。同时,UCSF也比较有名,虽然是分校,但在过去20年间,出了4个诺贝尔奖得主。我们呼吸方面几个比较有名的工作,都是这里提出来的:比如表面活性物质就是这里的John Clements发现的;血气电极就是这里的Severinghaus提出来的;哮喘的本质是炎症是这里的Jay Nadel
提出来的。大学也是理想的,导师也是心目中向往的,所以尽管我当时已经46岁还是很高兴地接受了这里博士后的位置。
记:您说过在UCSF做博士后期间是您事业的一个转折,为什么这么说?
白:那段留学经历确实是让我开拓了视野。原来在国内的时候,尽管我也很努力地工作,但总觉得自己提不出太多太新的东西,思维被限制住了,没有什么高水平的思路。到了UCSF以后,看到的、听到的、学到的跟国内大不一样。此外,在国内有时候尽管有想法,但却苦于没办法实现。到了那里,很多想法就有了实现的可能,因为从环境到试验条件大不一样。所以确实是开拓了眼界、增长了见识。
此外,在UCSF,也给我后来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提供了机会。比如我后来一直研发的荧光血气分析系统,最初的灵感就是源自UCSF。刚才我提到,血气电极法就是这里的Severinghaus提出来的,但是电极法有个局限——测定动脉血必须在体外测,那就要抽取病人的动脉血,反复监测就要经常做动脉穿刺,病人受的创伤比较大,也无法连续监测,这是电极法的缺点。我就想可不可以有新的方法?恰好当时我们实验室的Alan Verkman教授用荧光的方法测定细胞内的pH、氧分压、二氧化碳分压,给了我很大启发。我就想到,这一方法既然可以测定细胞内的,当然也可以测定血液中的,于是就萌发了用荧光法监测血气的想法。回国后花了十几年的时间,终于陆续地开发出pH荧光传感器、二氧化碳荧光传感器和氧分压荧光传感器,到现在为止,血气监测的几个传感器我们已经都开发成功了。
在UCSF时的科研也让我有很大收获,给我后续的工作奠定了基础。我在那里虽然只待了不到两年的时间,但就以第一作者发了一篇很好的文章——“水通道在肺泡液体转运中的作用”,发在《Journal of Clinical Investigation》。这个杂志是很受推崇的,即使美国医院呼吸科主任能有一篇文章发在该杂志也会觉得很光荣。回国后,从1998年到现在,15年的时间里,从那第一篇国际文章开始,我现在陆续已经在国外发表了100多篇文章。那篇文章还为我进入行业最好的杂志《美国呼吸重症监护杂志》(American Journal of Respiratory and Critical Care Medicine)当编委起了重要作用。以前该杂志在中国根本没有编委,去年在入选编委的时候,该杂志的主编就想到了我,专门邀请我到西北大学(Northwest University)去做了一次访问。跟我聊的时候他说,我当初那篇文章就是他审稿的,认为很好,他印象很深刻,所以该杂志第一次在中国选编委的时候,他就推荐了我。这就对我们以后发文章、甚至获得国际认可都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在UCSF学习的经历不光对我本人有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对我后来回到国内以后,我们这个学科的发展,也起了很多重要的推动作用。比如,我在去美国之前,我们科也有一些医生出国留学,但几乎都是医生自己联系的,或者是科外人员帮助的。我回来以后,陆续介绍了十几个学生到国外去进修、学习、做博士后。有的回来以后成了我们科的栋梁,在国内有一定的影响。所以这是一连串的作用。同时,对我们学科的发展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我在2002年6月28日接手主任以后到现在11年的时间里,我们学科的迅速发展和这个也有关系,使我能够建立一个接轨国际的医师团队、建立了两个创新实验室、建立了三大接轨国际的平台。
#p#副标题#e#
记:请具体谈谈您刚刚提到的接轨国际的医师团队、两个创新实验室和三大接轨国际的平台。
白:接轨国际的团队:我们科虽然只有40个医生,但是我们有3个医生在国外发表的文章影响因子都超过了300分。不光是发的文章多,这3位教授还经常受邀在国外作报告,还在国外各种学术团体、学会担任职务,还得到国外的各种奖项和认可。此外,我们还有多名青年医师和学生连续获得国际学会奖励。
所以我总结,我们有接轨国际的四有团队:国际大会有声音、国际杂志有影响、国际学会有位置、国际社会有认可。
两个创新实验室:一个是发展荧光血气分析仪的生物物理实验室。实际上临床学科很少设这种非常基础的实验室。我们设这样一个实验室的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发展荧光血气分析仪,来连续地、实时在线地监测病人血气。经过十几年的时间,我们也确实开发出了连续在线实时监测病人pH、氧分压、二氧化碳分压的传感器。现在整机已经研发得差不多了,我们希望将来能用在临床上。
还有一个是物联网医学实验室。物联网我们这里做得比较早。早在2008年,我就萌生了要做物联网医学的想法。当时我在国外参会的时候,看到有的学者在研究怎么样把病人的监测结果通过Internet传给医生,然后医生再反馈诊断治疗意见。我看了之后很受启发,这会给病人带来极大方便。但同时我也看出了他们的不足,病人只能通过互联网将结果传给医生,在中国就不一定实用。农村的农民或者城镇的市民,他们肯定有手机但不一定有电脑,即使有电脑也不一定有网可上。所以后来我就提出了基于手机的物联网医学。我们开发出了一些传感器,如测定肺功能的传感器。这样陆续就把物联网医学带动了起来。现在,我们不单将物联网用在监测病人肺功能,随后还将用在监测病人睡眠中的血氧饱和度、胸腹运动、口鼻气流,用来诊断病人在睡眠中有没有睡眠呼吸暂停问题,这已经开发得差不多了,而且建立了世界首个睡眠呼吸暂停物联网医学家庭监护和管理平台。
三大接轨国际的平台:第一个是杂志平台。在过去6年中,我们这里创办了两份国际杂志,一个是《Journal of Clinical Bioinformatics》(临床生物信息学杂志),由我们科的特聘教授王向东做主编,我做副主编,由BioMed Central出版社出版。另一个是我们创办的《Translational Respiratory Medicine》(呼吸转化医学杂志),我做主编,王向东教授做副主编,由世界数一数二的大出版社Springer出版社出版。我们的工作、学术影响受到了国内外的普遍认可。很多国际有名的专业期刊都邀请我们做编委,有的甚至是中国唯一的编委。最早聘我做编委的是《Chest》(胸),后来陆续有又有两个《American Journal of Respiratory Cell Molecular Biology》(美国呼吸细胞分子生物学杂志)、《American Journal of Respiratory and Critical Care Medicine(IF 11.08)》(美国呼吸呼吸和重症监护杂志)也聘我做编委,后者是我们行业最有名的杂志。此外,我们科宋元林教授是亚太呼吸学会会刊《Respirology》(呼吸病学)的副主编,王向东教授担任《Respiratory Medicine》的副主编,我本人是《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PD》(慢阻肺国际杂志)的副主编。所以我们科在国际期刊中的影响是很大的。
我们还有一个会议平台。2003年,我们科创办国际呼吸病研讨会(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Respiratory Disease,ISRD)。第一次举办的时候只有320人参加,我们邀请了26位国外的讲者,当时还没有外国人来注册参加。2005年以后,这个会议每年举办一次。第二次就有近千人参加,不单参加的人多、国外讲者多,而且每年国外都有50个~100个外宾注册参会听课,这是一个转变。我们国内很多国际会议只有外国的讲者,没有外国的听众,而我们举办的这个会议彻底改变了这种状况。最近4年,因为认识到ISRD的重要性,世界最大的胸科学会——美国胸科学会(American Thoracic Society,AST)就和我们办联合会——上海国际呼吸病暨ATS联合论坛(ISRD & ATS)。最近4年我们联合召开了4次会议,为国内外医生交流提供了很好的平台。而且我们还为国内青年医生提供机会,让他们走出国门,走向世界。比如说我建议ATS给中国青年医生专门设立奖项,鼓励他们出国学习。最近3年,我推荐成功88个35岁以下的中国医生去美国参会,ATS提供一定的奖励。这是破天荒的,其他国家从没在ATS享受过这种待遇,而且在ATS过去100多年的历史上,给中国的奖项总和也没这么多。我们的青年医生参加完这个会议以后非常高兴,因为他们有这么好的机会,不但获奖还学到了很多东西,让他们这么年轻就走向世界。所以,我们这个会议的宗旨就是:接轨国际、面向世界。可以用简短的几句话来描述ISRD & ATS:接轨国际新契机、直面名家近距离、启发创新有知音、走向世界助推器。
#p#副标题#e#
第三个平台是国际学会平台。我们科现在在国际学会中担任职务的人有很多。比如我担任过美国ATS科促会的委员,在我任职期间,21个委员中只有我一个人不是美国人。王向东教授担任过ATS国际肺健康委员会的委员。我和宋元林教授都担任过ATS呼吸细胞生物学会的委员。我本人还是美国另一个大型学术组织——美国胸科医师学院(American College of Chest Physicians,ACCP)的国际事务负责人、欧洲呼吸学会的中国首席代表、亚太呼吸学会科研委员会的主席。这不光对我们科对外交流有利,同时也有利于我们国内其他呼吸科医生与国外的交流。比如我任亚太呼吸学会科研委员会主席还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推荐或者批准了好几个中国人去拿这个学会的奖项,比如去短期进修,我就曾批准一个长春医生去澳大利亚短期进修3个月,所有费用,包括食宿、机票等全都由亚太呼吸学会支付。最近我又批准一个中国医生从中国去欧洲参加欧洲呼吸学会的年会,所有费用也都由学会负责。这对中国医生的对外交流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在此同时,我也认识到改革开放已经使中国经济走向世界,也应该使中国医学走向世界,我们不但需要学习国外,也需要国外向我们学习,需要有自己的国际学会,为此在二年前我即在香港注册了国际呼吸病学会(International Society of Respiratory Disease,ISRD),希望这一学会将来能为中国呼吸界影响世界发挥作用。
基于临床的发明
记:ATS会刊名人录曾称您为专注于发明创造的临床医生、科学家和导师,请谈谈您的发明创造。
白:我从小就对发明创造比较感兴趣。另外,在临床工作中我也感觉到,如果一个医生只会按部就班地重复前人的工作,就不能很好地为病人解决问题。要想发展就必须发明创造,来解决以前的不足,超越从前。正是因为这样,所以我才提出了两个创新实验室——生物物理实验室和物联网医学实验室。现在我们的物联网医学,已经马上就要应用到临床了,尤其在睡眠方面。原先,我们科只有4个监护仪,每天晚上只能监护4个病人。怀疑有睡眠呼吸暂停的人,到我们科要求检查,最长排队要半年多。有了我们的物联网医学应用到睡眠的诊断、管理,就大不一样了,我们科现在的诊断能力,从原来每天晚上接收4个检查者,到接收44个,翻了10倍多,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此外,我们还将在慢性阻塞性肺病(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COPD)和哮喘的管理上扩大物联网医学的影响。另外,在ICU方面:最近禽流感出现以后,我发现会诊很不及时。金山公卫中心要我去会诊,首先,我能不能马上就去?比如说我现在正在讲课或正在给其他病人看病,那总得先让我完成手边工作,再加上路上的时间,到达的时候可能就已经晚了几个小时,如果在外地出差就更不能及时赶到了。如果将物联网医学应用到这些公共卫生事件中,应用到病人的急救中,那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很快地在几十分钟内或者几分钟内进入状态,帮忙解决问题。
肺损伤发展到后期会出现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cute respiratory distress syndrome,ARDS),死亡率很高,但现在缺乏治疗方法。机械通气只能解决一部分问题,解决生命支持的问题,没有很好的治疗用药,现在唯一能用的药就是激素。而激素治疗ARDS是双刃剑,既可以让某些病人通过治疗好转,又可以给病人带来副作用,严重副作用甚至能夺取病人性命。目前没有更好的药。我们现在就在研发新的药物,希望将来能用于临床。这方面我们已经有两个比较成型的药物,一个叫表皮生长因子2,今年已经被授予发明专利。我们的研究结果发现,它有可能预防一些肺损伤病人发展到ARDS。另外,我们还在研究干细胞,我们最近也有一个干细胞专利,正在评审中。结果也表明,它对肺损伤的修复很重要。还有一个是中药,叫姜黄素。关于姜黄素的研究,在世界上我们是最早做的,发表在几个很有影响的国际杂志上,我们发现姜黄素能减少肺损伤,对抗肺的一些炎症因子,使动物的存活率明显提高。发表完文章后,我们也寻找过合作伙伴,看能不能把它转化到临床上。但遗憾的是,目前国内还没有什么企业有这个概念。但让我高兴地是,美国在我们之后已经想到把它应用到临床了,正在做临床验证。他们也承认是我在世界上最先做的动物实验得出的结果,启发他们去做临床,这是我感觉很好的一件事情。虽然我们国内没有成功用到临床,但国外成功了,将来都一样用于病人,这是好事。
所以我认为,科研和高水平的医疗是密不可分的。要想医学有所进步,就必须靠科研、靠发明来推动。这也就是我热衷于科研、热衷于发明创造的原因。到现在为止,我已经获得了27项专利。
记:您觉得怎样才能成为一名临床医学科学家?
白:我的大多数发明创造都跟临床有关,是临床工作给了我创作的灵感。我知道临床需要解决什么问题,而不是闭门造车,临床不需要的也在那发明,发明了临床也用不到。
我认为要成为临床医学科学家,首先要热爱你所从事的临床工作,这是非常重要的。从我做医生开始,我就立志一定要做一个非常好的名医。光有想法还不行,要成功还要有3个要素。我常跟我的学生讲,一个人能做成大事,无非是3要素:智商、悟性、勤奋。智商是很重要的,尤其对医生而言。如果智商不够,记忆力也不好,那就没办法学医。今天学、明天忘,永远不知道遇到下一个病人该怎么治。光有智商,没有悟性也不行,那是计算机一个。有了智商、悟性,又不用,懒惰,就是浪费资源。所以这3个要素缺一不可。
振兴科室
记:您是怎样带领科室崛起的?
白:2002年6月28日,我接手中山医院呼吸科主任的时候,盘点一下家底发现,到2002年时,科里没有拿到过自然科学基金,也没有以第一作者单位在国外杂志发表过文章。那时我就认识到,要想让我们科室兴旺发达、重振雄风是要下大功夫的。于是,我提出科研振兴学科,临床突出特色。
2002年底,我们科的奖金平均只有1000元左右的时候,我就定出奖励计划——平均每人从1000元里拿出一点,奖励在国外发文章的作者,影响因子1分到3分奖励3000元,3分到5分奖励5000元。从那以后我们科在国外发的文章多起来了。
后来我注意到,光发文章还不行,不能代表整体水平,应该接轨国际、面向世界,所以我就提出国际四有教授——国际大会有声音、国际杂志有影响、国际学会有位置、国际社会有认可。这样的话,目标逐渐提高,同时自己更要带头干。我提出四有的时候,没人怀疑,因为我首先就是四有,我先给他们做出了榜样,下边的医生陆续劲头就提起来了,大家从过去的混小日子,搞自己的事情,变成关心学科、关心学术。我很高兴最近几年青年人发的文章很多,刚毕业1年的学生有的已经发表4篇5分以上的文章了,再加上其他第一作者的文章,影响因子就有40多分了。可以这样讲,首先要有目标,然后自己带头做,给大家做出榜样。另外,奖惩机制要清楚,得赏罚分明,这样大家就有劲头了,成果会越来越多,学科影响就会越来越大。
此外,我们不光抓科研,还抓临床。临床我们原来有几个特点:呼衰和感染。我想光靠这两个还不行,还得搞一个肺癌,所以2002年1月28日我就联合胸外科、放疗科建立了中国第一家肺肿瘤综合诊疗中心。此外,我在临床还做了两件事情:第一,设立专病门诊;第二,开展特色技术。我在接手做主任的时候只有两个专病门诊,一个是三科门诊,一个是哮喘门诊,后来我又加了16个专病门诊,所以现在我们有18个专病门诊,而且其中有好几个是中国第一个:比如高原门诊、胸膜肿瘤门诊和肺真菌门诊。其他还有靶向治疗门诊、肺结节门诊等,都是国内比较早开设的。我们还有28项特色技术,包括物联网医学演化出的6项(物联网哮喘特色技术、物联网慢阻肺特色技术、物联网医学睡眠诊断、物联网医学睡眠治疗、物联网医学ICU、物联网医学肺功能特色技术)。
(作者:白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