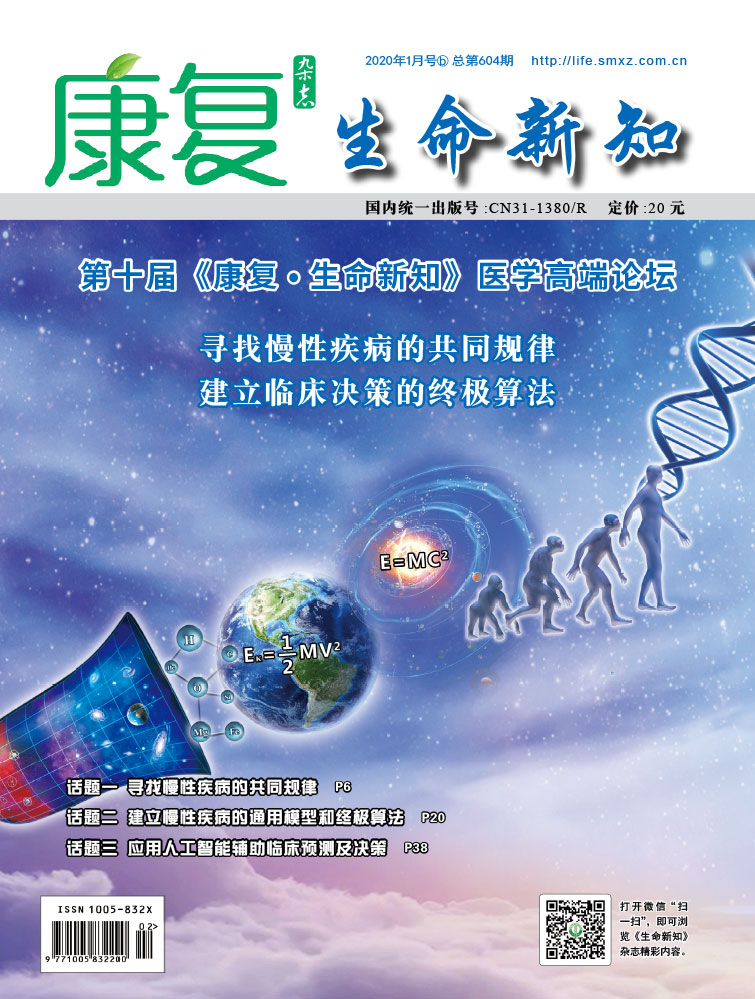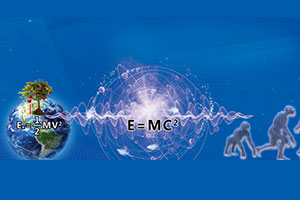作者:刘艺红
历史的长河,孕育出许多大师,他们通过对大自然的观察、思考、分析、总结,找到自然现象的共同规律,并通过提取模式、建立模型、设计算法,形成了解析自然、预测未来、改变世界的科学定律。苹果落地激发牛顿逆向演绎(inverse deduction),悟出了万有引力法则,解析了潮汐与日月;一梦醒来,门捷列夫逆向回归(inverse induction),诞生了元素周期表,预测未知元素;克里克和沃森通过逆向解析(inverse engineer),将散落的碱基排成双链螺旋,一元化解密生命;爱因斯坦从经典力学模拟推理(analogic inference)出了E=MC2的著名公式,揭示了质量与能量互换的算法。而这一切的一切,均基于宇宙的共同起源,以及时间、空间、物质、能量在微观及宏观的运行本质。同理,地球上的生命具有共同的起源,并遵循着适者生存的自然选择规律,不断繁衍和进化,塑造出生物多样性,以及伴随着基因、环境、习惯及运气交集的不同种系的表观及疾病。Darwin据此发现了物种起源的规律,提取了自然选择模式,建立生命进化的模型,设计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终极算法;而人类的生、老、病、死既然有其共同运行规律、共同分期、共同治疗思路及共同目标,让我们静下心来思考:我们能否像大师一样提取慢性疾病的通用模式?建立人类慢性疾病的通用模型?设计出健康与疾病的终极算法?
一、慢性疾病的发展是否有规律可循?
在第十届《康复•生命新知》医学高端论坛上,300余位来自全国各地的医学专家投票显示:42%认为慢性疾病的发展大部分有相似的病理过程,46%认为大部分有相似的临床病程,这两个选项的占比都非常高,余下只有12%的医学专家认为大部分慢性疾病的病理或临床病程不同。
主持人肖飞教授:
Doctor Chong, you are an immunologist, you developed immunosuppressive agents based on the lab discovery, and also you found every foreign organ has immune problem, and also you put effort on not only treat rejection, you also want to induce tolerance, so what’s your view about the common pathway from a transplantation aspect?
(Doctor Chong,你是免疫学家,你和你的团队基于实验室研究开发了免疫抑制剂,你们发现所有移植的器官都存在免疫问题,你们不仅仅要治疗排异,还要诱导耐受。从移植学的角度来看,你认为慢性疾病的发展是否有规律可循?)
Anita Chong教授:
From immunologist point of view, we are very interested in understanding basically what happened to the immune system. If you divide the immune system into two major parts, you have the part that is what we called innate, and there is the part what we called adaptive, adaptive has T cells and B cells, and the processes in which the adaptive and innate induce injury are very different. If we look at the T cells, a lot of immunosuppression that we have are directed and preventing T cell responses, and then we also have some drugs that affect and control B cell responses. What we have fewer are drugs that control the adaptive immune system, things like steroids, so what we would like to do as an immunologist is to understand exactly which part of the immune system is causing the disease, and then trying control them. You need your immune system, if you just have a general way to just control all your immune system, you will have no autoimmune diseases, you will have no rejection, but you will have a lot of infections. So for us what we want to do is understanding specific mechanisms and then coming up with ways to control specific arms of the immune response.
(从免疫学的角度看,我们对从根本上理解免疫系统如何运作非常有兴趣。免疫系统主要分为两大部分,即固有免疫(又称非特异性免疫)和适应性免疫(又称特异性免疫或获得性免疫),适应性免疫又分细胞免疫(T细胞参与)和体液免疫(B细胞参与)。固有免疫和适应性免疫的运作过程是非常不同的。现有的很多免疫抑制药物能直接阻止T细胞的反应,同样也有药物可以影响和控制B细胞的反应,但我们缺少的是可以控制适应性免疫系统的药物,例如类固醇。作为免疫学家,我们需要准确理解免疫系统的哪个部分在导致疾病,并且试图控制这个部分。同时我们也需要自身的免疫系统,如果只是采取一个通用的方法控制了免疫系统的全部,人类将不会患自身免疫性疾病,也不会有排异反应,但却会大大增加感染的危险。)
肖飞教授: 刚才Doctor Chong讲的是我们的免疫系统分两大部分,一个是获得性免疫,另一个是固有的免疫。我们希望控制因免疫失常而导致的疾病,但同时要把我们自身的免疫系统维护好,避免在控制自身免疫疾病和移植排异反应的同时失去了自身的免疫力,反而患了其他的疾病,因此需要掌握平衡,维护内环境稳定。我非常赞同她的观点。
主持人肖飞教授:
So Doctor Baeten, Like Cimzia, it can treat not only the rheumatoid arthritis, but also ankylosing spondylitis, and psoriatic arthritis, etc. So, any comments?
(Doctor Baeten,像希敏佳这样的药物,不仅仅可以治疗类风湿关节炎,还可以治疗强直性脊柱炎和银屑病关节炎等,对于慢性病的共同规律,你有什么看法吗?)
Dominique Baeten教授:
You probably suppose I would say A or B, but my answer is still C, so now I am here with my head of a clinician academic research not from a pharma. As we know TNF is a common target for both rheumatoid arthritis and ankylosing spondylitis. When many years ago, I started my own research group in academia, one of the most intriguing questions to me is why blocking TNF is so effective in two diseases at least two completely different phenotype and progress, and we spoke a little bit this morning about TNF, and one aspect is TNF is produced as a molecule that’s both transmembrane and soluble, so it can be cleaved and it can become soluble TNF. We use animal models to mimic that, but we also looked at patients. What we recently discovered is that if you mainly express soluble form of TNF in mice, you get the phenotype which is completely rheumatoid arthritis, if you express exclusively the membrane form of TNF without soluble TNF, you get the full ankylosing spondylitis phenotype with new bone formation, everything that you see, so what I learned is that in this case the same cytokine but acting slightly differently may lead to a completely different pathway, pathology and progress, that is TNF example. We can discuss the same about IL-23 and IL-17 pathway, why blocking IL-23 is very effective in psoriasis not ankylosing spondylitis. There are many examples across the fields, we discussed a little bit before about hepatitis and fibrosis, we know when we cure patients from hepatitis C, a large proportion of patients’ fibrosis stopped or even resolves, but 22% and 25% of patients’ fibrosis is still proceeding, so for me it’s still amazing about how to differ these processes.
(你可能觉得我会选A或B,但是我的选择是C,我是从临床学术研究的角度出发做出的选择,而不是从药物的角度。TNF是类风湿关节炎和强直性脊柱炎的共同治疗靶点,我觉得最有趣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TNF抑制剂对两种疾病(具有两种完全不同的表型和病程)都有非常显著的功效?我们今天上午也谈到了TNF,TNF可与细胞膜结合成为跨膜型(或膜结合型)TNF, 也可进入体液成为分泌型(或可溶型)TNF。我们使用动物模型模拟,但同时我们也会观察患者,最近发现,如果在小鼠体内主要表达可溶型TNF,就会出现类风湿关节炎的表型,如只在小鼠体内表达跨膜型TNF,则会出现强直性脊柱炎的表型(包括脊椎赘骨生成等强直性脊柱炎的所有症状)。从以上的发现中可以总结出,对于同一个细胞因子,即使微小的改变也可以导致疾病的病程和病理完全不同,这是TNF的例子。白介素23和白介素17也是同理,为什么阻断白介素23对于银屑病非常有效,但对强直性脊柱炎无效?在各个领域中都有很多类似的例子。我们刚刚谈到了肝炎和纤维化,我们知道,当治疗丙型肝炎患者时,会有很大一部分患者的纤维化停止甚至消失,但22%和25%的患者纤维化仍在继续,所以对我来讲,如何区分疾病的进展仍然是令人惊叹的。)
栗占国教授:
我的回答是A,我认为大部分自身免疫病有类似的病理过程。我们今天在座的多数专家都来自自身免疫病领域,这类疾病的基本免疫学原理是:由于抗原介导的T细胞活化,后来B细胞参与,引起相应的炎症反应,当然同时受遗传因素与外界因素(例如微生物、病毒等)的影响,从而引起免疫反应,然后出现相应的下游免疫系统紊乱、细胞紊乱,再出现因子紊乱,所以导致了一些炎性因子的增高,一些抑炎因子的减少,最终导致了自身免疫性疾病。大部分患者经历了此过程,但有些患者因为某一个因子或者某个细胞是特殊的,从而出现了异质性。例如TNF-α抑制剂,在治疗疾病和研究中发现,TNF-α抑制剂对多数患者都有一定效果,对一部分患者非常有效,对一部分患者效果差一些,对一部分患者另一类药物更有效,因此体现出了异质性。所以在大的发病规律前提下,应找到不同患者的免疫学和病理机制来做相应的研究和临床应用,这其实引出了精准的概念,所以要针对特定疾病的特定细胞群生成的因子来干预,以使多数患者得到比较好的缓解,下一阶段治疗是将“大部分”和“个别”结合起来形成联合用药,多种细胞因子多靶向干预。
Anita Chong教授:
I think one of the big differences between people who treat auto-immune disease and people like me who are interested in transplant is that by the time rheumatologist sees the disease is already many many years after immune response has already developed, so what you see is the tissue that was already damaged, I think many common mechanism automatically lead diseases to the pathology that is similar which is a lot of cells infiltrating your tissue, which is inflammation. I think in transplant what we have is that we know when the disease start, when the graft is put in, and if we monitor overtime, we can see which part of the immune system is escaping the immunosuppression, and causing the damage, at the beginning the damage is very different, but automatically the damage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similar, so I think that if you are an immunologist like me, you study mechanisms, and all the differences of all the different types of cells, all the different cytokines, like Professor Baeten has said, even different types of the same cytokine whether it’s membrane or it’s soluble, causes different type of disease, I think that could give you a lot of power in terms of individualized medicine. Even though if you look the common pathway in a very far far away, it looks exactly the same, so it’s up to you whether you want to look it as if it’s same from very far away, so you use same therapy and same approach, or like me, where you say everything is different, you can individualize the treatment, and preserve all parts of immune system that is necessary to maintain good health.
(我认为自身免疫疾病领域的医生和移植免疫学者相比最大的不同是,当风湿科医生看到疾病时,免疫反应可能已经发生很多年了,患者组织已经受损。我认为共同的原理所引发的疾病自然会发展成为类似的病理,即大量细胞渗透组织,即生成炎症。但在移植领域我们可以看到疾病的开端,即将移植的活组织植入患者体内时,如果实时监控,我们可以看到免疫抑制药物对免疫系统的哪个部分没有发挥作用,因而造成了部分的机体损伤。在开始阶段,损伤有很大的不同,但是损伤会自动变得越来越相似。我们免疫学者主要研究所有不同类型细胞和不同细胞因子的区别,以及它们之间的作用机制,正如Professor Baeten刚讲的,即使相同细胞因子的不同形态(跨模型与可溶型)也会导致不同的疾病,这为个体化医疗这一理念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如果你从非常宏观的层面看,所有的慢性疾病都有共同的规律,可以采用相同的治疗和方法,或者也可以像我一样从疾病起始的微观层面看,那么一切都是不同的,应采取个性化的治疗方法,保护整体的免疫系统以维持健康的状态,所以这取决于看待疾病的角度。)
主持人肖飞教授:
Doctor Chong提到了一个非常好的观点,从她移植免疫学家的角度看,当自身免疫疾病的医生看到临床患者时,器官损害和临床症状已经形成,因此风湿科医生看不到疾病的开端。当器官移植到患者体内时,免疫反应就已经开始,所以移植免疫学家可以看到不用因子的不同表现,这给Doctor Chong一个启示:随着疾病的发展最后所有表现趋于一致,但是我们可以从最开始控制很多起始因子,从而走向个性化的治疗。
栗占国教授:
我补充一点,我很赞同Doctor Chong的观点,我们自身免疫病的治疗或研究都主要对抗下游因子虽然也很重要,但我认为,从长远看,做研究还要着眼于疾病的开始。
主持人肖飞教授:
这也提出了一个早期治疗的问题,早期治疗也需要多学科合作。Doctor Chong他们所做的模型是移植免疫模型,移植免疫学家将异体器官植入模型中,异体器官对模型而言即大量的抗原,从而激发模型产生自身免疫反应,所以移植免疫学家可以看到疾病和免疫反应的起源。因此我们需要多学科合作来控制自身免疫这类“暗能量,暗物质”。
沈锋教授:
对于这个问题,我引用一句中国的官话,“上面同志们的发言我都赞成,都说得对”。如果将病理过程落实到炎症,那么大部分慢性病都有相似的病理过程。如果将病理过程落实到一些非常细的方面,比如某些基因的突变而导致一些病理表征、表型的变化,则有区别。
从我的领域看,我选择B“大部分有相似的临床病程”。列举三个临床例子:
第一个例子是乙型肝炎(hepatitis B) 和丙型肝炎(hepatitis C)患者,这两种疾病的病理有细微的差别,但临床表现却基本一致;
第二个例子是肝细胞癌(hepatocellular carcinoma,缩写为HCC,中国高发)和肝内胆管癌(intrahepatic bile duct carcinoma),这两种肝癌有相似的临床病症和病程,但病理却不同。肝细胞癌主要来源于肝细胞病毒感染,感染的肝细胞通过一些代谢的途径呈现出其特征性的表现,比如ADG1,ADG2的突变等等,不同的表现型治疗方案也不同;肝内胆管癌与胰腺癌特别相似,突变都是以TP53、KRAS这些炎症的信号通路的突变为主,所以肝内胆管癌与胰腺癌的恶性程度都很高。
第三个例子,两种类型的肝内胆管癌都有相似的临床表现,例如肝脏肿块、压迫胆管引起黄胆、晚期患者的恶病质等,但两种肝内胆管癌的病理却完全不同。
主持人肖飞教授:
Actually we are putting together a big puzzle, as we each have a different point of view (including phenotype, genotype, pathophysiology, molecular biology and molecular signal transduction) , so we put them together to make the definition of disease, classification of disease intact.
(现在我们就像在做一个大拼图,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观点(表现型、基因型、病理生理学、分子生物学和分子信号传导等),我们把这些观点拼到一起,从而使疾病的定义和分类更加完整。)
孙凌云教授:
我的答案是ABCD。
主持人肖飞教授:
Doctor Chong是从我们的信号传导、分子生物学角度分析,Doctor Baeten和栗主任从病理学角度分析,沈锋教授是从临床表现的角度, 而孙主任的选择是ABCD。
孙凌云教授:
我是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来看这个问题,换句话说,4个选项都不一样,但都可能发生,所以我认为是ABCD。
从宏观层面看,慢性疾病都是因免疫失调引起炎症反应,所以病理和临床病程相同,都给患者带来痛苦,只是痛苦的表现不同,有的疼痛、有的发烧、有的器官功能异常,总之最终都走向死亡,如治疗顺利可以延长患者生存期,治疗失败则会缩短生存期;但换个角度看,不同疾病的病理和临床病程又不同,例如骨性关节炎,部分患者没有症状;高血压和高血脂,如治好不会对患者造成影响;但系统性红斑狼疮,如治好患者的生存期可以非常长,但治不好则会危及生命。
从微观层面看,慢性疾病的发展完全不同,例如TH17在银屑病、关节炎、类风湿关节炎的表现都不同,刚刚提到的TNF-α的例子也同理。
不同疾病既相似又不相似,所以很难回答,我可以回答四个选项都对,也可以回答一个都不对。
主持人肖飞教授:
这个题目很有意思,有争议,大家将来可以再继续这个话题,看看哪些相似,哪些不相似,可以多学科来回答这些难题。
二、疾病趋势的预测
300余位参会的医学专家中,有高达73%的医学专家认为自己对疾病发展趋势的预测能力比较强,经常可预测到疾病的发展趋势及预后;7%的医学专家认为自己这方面的能力很强;15%的专家认为自己这方面的能力一般,偶尔能做出正确的决策;极少数专家(5%)认为无法预测,疾病随时千变万化。
孙凌云教授: 我选A,我认为作为一个临床医生必须要有自信,当然自信来源于临床经验,没有丰富的临床经验就不可能有很强的预测能力。
主持人肖飞教授:
您的预测准确率有数字吗?
孙凌云教授:
我没具体计算过预测准确率,准确率即抢救成功的患者概率。临床医生必须要有预测能力,例如一位狼疮性肾炎患者来就诊,狼疮的表现是不同的,但我们科的很多医生,也包括很多今天在座的一些医生,都先给患者服用大约60毫克激素,我认为这是不正确的,如果都按照教科书上的每公斤体重2毫克激素来治疗,那治疗后会引起很多患者一连串的副作用。
主持人肖飞教授:
所以临床和教科书不一样。我再多问一句,孙主任,你有预测错的时候吗?有总结吗?
孙凌云教授:
人总归有错的时候,患者死亡就是我预测错了。
主持人肖飞教授:
有时患者死亡也很无奈,未必是因为预测错误。
孙凌云教授:
因为生命太多奥秘了,存在许多未知,意外也会发生,大家都可以理解,飞机也会失事,很多事情都不可能100%顺利。
沈锋教授:
我的回答的是B,我们临床上有一个量化的预测指数是C Index(Concordance Index),用于衡量预测和实际发生情况之间的符合度,C Index一般应在80%左右,超过80%的则为优秀,70%~80%为良好,60%~70%为一般,低于60%为不合格。之前我的一位老师跟我聊过这个话题,他认为我们预测成果还不理想。C Index 80%是什么概念呢?即在100个患者里面预测某个事件,有80个患者应验了你的说法。例如,我认为患者病理上会出现哪个症状,病理结果100个人里有80个患者出现我说的症状,那么C index是80%。
主持人肖飞教授:
你有数据吗?
沈锋教授:
我们每一项工作都用C index衡量。
主持人肖飞教授:
国际上有个标准叫ROC。
沈锋教授:
AUC、ROC都可以,计量化是最简单的方式,即C index,每一项都需要单独计算,我认为我们目前达到的水平在78%~82%左右,我的选择是“比较强”,这是由大数据得来的,通过统计学的多因素分析能够得到一个比较精确的预测。但为什么不是最强呢?因为刚刚Anita讲到的个体化治疗,有些患者的表现超出了预测范围。例如,我们经常会碰到某个患者手术非常成功,但最后这个患者可能两三个月后就转移了,肿瘤患者经常会发生这种情况。
主持人肖飞教授:
刚才他提到了C index,其实国际上还有个衡量标准叫ROC(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即把真阳性率和假阳性率绘制成一个曲线,如果在0.8以上,则有意义,而且意义非常大。现在预测自杀的ROC只有0.6,就像抛硬币一样。在临床上还有很多事情都没办法预测。
Doctor Chong, you do basic research, you design the protocol for a lot of projects like anti-virus, immune suppression, xenotransplantation etc. So what’s the successful rate from your perspective?
(Doctor Chong,你做基础研究需要设计很多项目的方案,包括抗病毒项目、免疫抑制项目和异种器官移植项目等。从你的角度看,(预测)成功率是多少?)
Anita Chong教授:
Good enough to still be here. It depends, I think that in our field, there is a lot of effort trying to balance sensitivity and specificity. So the more sensitive you are, there is also going to be a higher probability that you discover different ways from what is normal or healthy, sometimes it will be OK, sometimes you have to treat, so that’s what our field in clinical is really interested, which is trying to balance too. For instance, in mouse models for type 1 diabetes, we know that you have antibodies against the component of the islet, the more types of antibodies you have, the more likely you are going to develop type 1 diabetes. Because it’s children, you don’t want to start treatment too early with immunosuppression because they are kids you don’t want to give them drugs if you don’t have to, so the question is when do you start treatment? And some of those kids will never develop diabetes, but you give them drugs. You start to give drugs if the 80% will develop diabetes, I think this is the critical balance. I think in transplant, also for a long time, for instance in kidney transplant, by the time you discover serum creatinine, your kidney function is already very poor, so you should start treatment the moment you discover it, by that time your treatment may not be very good, so you want to start treatment earlier, so in our field we are trying to look at urine from the transplant to see if there are any changes that are consistently predicting as well as serum creatinine but a lot earlier, then start treatment, so I think the balance of sensitivity and when you want to start treatment is really really important.
(好到还可以坐在这里~开个玩笑。事实上看疾病情况而定。在移植免疫领域,我们做了很多努力来平衡敏感性和特异性。机体越敏感,越容易发现不同于健康或正常组织的异物,有时这不会对机体造成影响,但有时必须采取干预治疗,这也是我们移植免疫领域在临床研究中真正感兴趣的点,即试图找到平衡。
例如,人体有对抗胰岛成分的抗体,在1型糖尿病小鼠模型中发现,抗体的类型越多,小鼠越可能患1型糖尿病。1型糖尿病一般从儿童和青状年开始发病,因为患者年龄较小,医生不想过早的开始免疫抑制治疗,那么应该什么时间开始治疗呢? 一部分儿童将永远不会患糖尿病,但是医生还是对他们进行了药物治疗。如果患糖尿病的可能性为80%,则开始药物治疗,80%即为关键的平衡点。
在移植领域,相当长的时间内,当发现问题时往往已为时过晚。例如肾移植,当发现血清肌酸酐时,患者的肾功能已经很差了,所以一经发现,应立即开始治疗,但治疗效果可能不会很理想。所以,在我们领域,我们会持续观察患者移植后的尿液,以寻找其它可以较早预测疾病的成分。所以,我认为敏感性的平衡与开始治疗的时间都非常重要。)
主持人肖飞教授:
所以Doctor Chong强调了两点,即敏感性和特异性,敏感性与特异性组成了生命的平衡。她说在1型糖尿病经常会发现自身抗体。自身抗体出现的时间和治疗开始时间都很关键。治疗不能开始太早,太早会对儿童造成损害,太晚则错过治疗机会。移植也是同理,例如肾移植,当检查出尿肌酐上升时,一般已经比较晚了,所以我们应实时检测,以发现尿液中其它可以更早地预测疾病的成分,避免错过治疗时机。
栗占国教授:
不同专业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可能不一样。刚才沈院长选B,因为外科是真的高风险,变数较多。在我们内科,相信很多人选的答案是A。我同意孙凌云教授的说法,如果医生有丰富的经验,在患有内科疾病的患者(例如狼疮)入院后,医生基本能够判断出患者的转归。
主持人肖飞教授:
您觉得是经验的积累,还是您积累了很多的数据和参照标准
栗占国教授:
主要是经验的积累,临床经验非常重要。我们科室有个基本的规定,即要求为所有入院的重症患者做评估,将患者所有的临床表现和实验室变化的指标列一个表,根据这个表可以判断患者的预后和用药转归。
Dominique Baeten教授:
My answer is C, I think we are becoming really good in diagnosis, fortunately we are getting better and better in treatment, as a clinician I still struggle about predicting what will happen to patients. I give you 2 examples, one example is predicting a patient with Ankylosing Spondylitis whether she or he will develop ankylosis, B27 can give you some direction, but doing a real prediction is very tough. The another example, we were just discussing this morning, we discuss RA in pregnancy, we said probably more than half of the patients are doing a little bit better during pregnancy, the other is not, I have no idea how to predict when she come to see me and ask me whether she will be better during pregnancy, so from clinical perspective I still struggle, but I am very happy that we have colleagues that are better. From private perspective, I would like to ask the help later on, maybe they can help me with better prediction.
(我的答案是C,我认为现代医疗在诊断方面做得很好,幸运的是我们在治疗方面也越来越好,但是作为临床医生,预测疾病的发展趋势对我来说依然很难。
举两个例子,一是预测一位强直性脊柱炎病人是否会患关节强直(ankylosis),可以参考B27,但是真正的预测还是非常困难;
另一个例子是关于妊娠期的类风湿关节炎患者,今天上午我们刚讨论过,可能超过一半的患者妊娠期病情会好转,另外一半则并非如此。当RA患者咨询我是否妊娠期病情会好转,从临床的角度看,预测依然很难,但我很开心我们有同行在这方面更强。我很想稍后私下请教一些同行,希望对我未来的预测会有帮助。)
主持人肖飞教授:
Doctor Baeten很谦虚,他回答的是C。所以作为临床医生,我们现在的预测手段依然非常少,所以还会遇到很多问题,例如TNF-α的治疗,哪些有效、哪些没效,还有很多实际的临床问题待解决。
三、当联合用药发生不良事件,怎样调整方案?
对300余位医学专家展开的调查显示,当一种联合用药发生不良事件需要调整方案时,绝大多数医学专家采取的行动是根据经验判断,撤掉不良事件发生率最高的药品,比例占所有投票人数的60%,只有11%的医学专家利用大数据及算法辅助撤药,可以看出,在医疗领域,目前大数据和算法的应用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Dominique Baeten教授:
Probably be either A or C, depends on if there is a good reason that the lastest drug I add will induce adverse event, otherwise it’s based on clinical experience of myself and colleagues, that’s probably how I would do it.
(可能是A或C,取决于是否有理由证明最新加的药会引发不良反应,否则将基于我个人和我同事们的临床经验。)
栗占国教授:
我认为多数专家会选C,我也比较同意C,因为临床经验非常重要,根据过去的用药经验,我们了解哪种药发生某种不良反应的概率最高。
例如,根据经验判断,不同药物的不良反应发生率在不同部位可能不同,例如生物制剂也许对肝肾影响比较少,所以如发生肝肾的不良反应,则其它免疫制剂导致的可能性更大。
Anita Chong教授:
Well, as I am not a physician, if I have to guess, I would try D, because I have been convinced that if Cinkate Group have a big data, you have all the different drug combinations, and you have all the different side effects, eventually you will be able to determine what exactly is the right answer. The experience or reading the brochure is not going to be enough.
(我不是医生,如果必须要选,我会选D,因为我知道欣凯集团有大数据库,我相信,大数据涵盖了所有的药物联合、所有不同的副作用,最终大数据将能够判断出哪一个是正确的答案。经验或说明书都是不足够的。)
沈锋教授:
我的选择是C。我用了排除法。关于A,如果撤掉最后一个药品,并不能排除是因为前面这些药到了一定的时间而导致副作用的可能性,所以A是不合理的。B是看说明书,大家都知道说明书是什么,打个比方,如果所有的药都有肝功能损害,当出现肝功能损害的时候,仍然无法判断是哪个药引起的。D当然好,但是至少在我们这个领域里面,关于药物的应用,大数据及算法仍有待提高,所以通过排除法我只能选择C。
举个例子,是我亲身经历的事情。我的老师在接受治疗期间,一天晚上睡觉时唤不醒他,大家都很着急,怎么会无法唤醒呢?他的生命体征完好,医生紧急安排他去做磁共振,磁共振结果显示也没有任何问题。后来有一位经验丰富的医生说,有一个药物正常剂量下出现不良反应的概率只有千分之一(0.1%),但是老年人不良反应的出现概率是5%,所以紧急撤掉了这个药物。结果此药物一经撤离,我的老师半夜苏醒了,也没有任何不良反应。通过这个例子,我认为经验很重要,这位心内科医生的经验非常丰富,所以我认为C是正确的。
主持人肖飞教授:
这是用先验知识推导了未来预测,与天气预报同理,事实上是先积累了大量的数据,用这些数据推导了未来。
孙凌云教授:
联合用药有多种方式,一种是一开始就使用两种、三种甚至四种药,如发生不良反应,医生首先要根据经验判断是哪种药物导致不良反应的可能性最大,如无法判断,则需要把可能发生不良反应的药物都撤掉。
所以在治疗类风湿关节炎时,我在临床上采取的方式是逐个递增药物,比如我增加了一个药物,如半个月或一个月后患者没有不良反应,且病情得到了很好的控制,我将不再增加新的药物,如患者的病情没有得到很好的控制,我再增加第二个药物,第三个……通过这种方式,如果患者发生不良反应,我将知道是哪一种药物导致的,这非常重要,如若无法判断,那么治疗将非常困难。
主持人肖飞教授:
如果加到最后一个药物后出现不良反应,你怎么撤药?
孙凌云教授:
这种情况就是A和C。我最开始选的是C,但如果最后一个加的药品出现不良反应,A和C都有可能的。
主持人肖飞教授:
我们医生都很棒,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当遇到临床问题时,通过说明书和经验判断,最后可以预测我们的未来,但我相信还有其他的一些方法。
四、当您的预测及判断与患者病情发展规律不符时,主要原因
多数专家(56%)认为当预测及判断与病人病情发展规律不符时,主要是因为可获得的数据太少,25%认为是经验导致失误,只有少数专家认为是循证医学证据误导和处理数据的能力有限,分别为10%和9%。
孙凌云教授:
首先需要判断疾病的诊断有没有错误,如果诊断错误,治疗将是盲目的。假设治疗有问题,我个人的观点是,现在的治疗有两个问题,一是剂量太高,另一个是联合用药太多。好多患者是被治死的,如果有些患者没有接受治疗,有可能不会感染。自身免疫病中的狼疮,死亡的第一原因是感染,感染当然与患者自身的免疫力下降有关,但很大一个原因是医源性的感染,这一点始终是临床医生需要关注的。作为临床医生,可以治不好患者,但不能给患者带来危害,例如造成严重的不良反应,甚至导致患者死亡,这是我们作为医生不愿意看到的。
主持人肖飞教授:
西医的鼻祖说do not harm,就是首先不要伤害患者。确实,美国的第三大死亡原因就是医疗失误。
沈锋教授:
我选D。从肿瘤学的角度看,医生预测错误的现象也很多,我刚刚提到,预测错误的概率在20%左右。大家都说数据比较少,但我认为现在的数据并不少,无论临床、病理或基因,至少在我们肝癌领域数据非常多。通过这些数据,我们可以进一步认识哪些患者是特殊的,必须要进行个体化治疗。
但我个人认为,在肝癌领域我们处理数据的能力是比较差的。我与大家分享一个例子,现在有很多测序公司,通过测序可以找到靶向治疗,但是我们通常会发现两个不同的公司测序结果是截然不同的,我们不能判定哪个公司的测序是错误的,因为可能是解读信息的方式不同导致测序结果不同。目前在国内外,生物信息学分析的能力都有待提高,为研究者、临床医生提供一个确定性的结论是非常重要的。
Anita Chong教授:
My answer is C, as a researcher we always believe that there is the right reason for why something works differently or the same as you predict, so I think in disease if you agree that they all have a common mechanism, and you look at pathology, inflammation, immune mediated, you think everything is the same, so it should behave in the same way.
But I earlier made the argument that even though it’s immune, there are many many reasons, many many different types of cells, there are many many different types of molecules, that might be initially causing the process, also I think the genetic of the person who has the disease can also affect how quickly the disease progress especially in transplant, so I think in the end there is always not enough data. If you exactly know the person, the cause, when, how long the disease has been going, I think you will be able to treat it and predict its course, but we just don’t have enough information.
(我选择C, 作为研究者,无论预测与实际发展一致与否,我们相信总有合理的解释。
如果你认同慢性疾病有共同的规律,你会认为病理、炎症和免疫介导等等都是相同的,所以疾病的表现也应该是相同的。
但我之前说过,仅仅免疫系统疾病也有很多原因,存在太多不同类型的细胞和不同类型的分子,这些元素都有可能是最初引发疾病的原因。另外,我认为尤其是在移植手术中,基因也会影响疾病进展的速度,所以最后总是没有足够的数据进行预测。如果能够准确了解某位患者,包括其病因、疾病开始时间、持续时间,则能够准确治疗并预测病程,但我们并没有足够的信息。)
栗占国教授:
我认为,现在看来B比较现实,但是我期待C和D将来会更好。大数据、算法现在有些难以想象,但5年、10年后能力可能会非常强。
Dominique Baeten教授:
I don’t agree with everything that was said, certainly on the “too little data available” part, I like this question, because I want to make a comment about B, I think this is a very interesting one, not only in medical decision making, but also in business decision making in science, probably also in personal life. The more experience you get , the more your brain is getting lazy, that’s how human brain works. What we start to do is because we have experience. We try to scan the world around us, instead of collecting all individual data points, we just select the data points to confirm our belief and our hypothesis, so it’s not because we have too little data, the truth is we give different weight to data. 80% of the time we are right, but 20% of time we are misled by our experience.
Let me share a very interesting study about medical decision making happened in hospitals, where researchers ask the question ”when do you have the best decision?”, The young fellow spent hours and hours going far to the patients’ , because she or he didn’t know the data. Then a professor came in, within 5 minutes he recognized a pattern. The answer is neither of them, between both of them discuss together that comes to the best decisions. So too little data? but also be careful about waiting the data in the wrong way.
(我不同意前面专家关于这个问题的观点,尤其是“可用的数据太少”部分。我喜欢这个问题,因为我想针对B谈谈我的看法,我认为答案B(经验导致失误)非常有趣,B不仅仅发生在医疗决策中,也发生在科学领域的商业决策甚至个人生活中。你获得的经验越多,你的大脑就越懒惰,这是人脑的工作原理。我们倾向于做我们有经验的事情,并且我们试图扫描我们周围的世界,不是通过收集所有的个体数据,而是选择部分的数据来证实我们的信念和假设,所以并不是因为数据太少,事实是我们对数据抱有偏见。80%的情况下我们是正确的,但20%的情况却因经验导致了失误。
我来分享一个关于医疗决策的有趣研究。在医院中,当医生被问及“你什么时候做的决定是最好的?”一位年轻的医生花了数个小时去病人的家,因为他(或她)没有数据。后来一位教授走进来,5分钟内这位教授总结了一个规律。答案是他们两个都不对,事实是他们一起讨论才可以做出最好的决定。所以是可用数据太少吗?我们也需要警惕用错误的方式等待数据。)
五、算法在临床实践及科研中的应用
300余位专家对于算法的应用,答案比较分散,25%的专家在临床实践及科研中对算法有体会,在有意识地建立和使用算法;32%无体会,在无意识中建立和使用算法;20%没体会,刚意识到算法;23%没体会,一直靠直觉。
Dominique Baeten教授:
A , it relates with my previous answer,I think in clinical practice, whenever you have hypothesis, the tendency of your brain is to confirm the hypothesis. I think we have to intentionally force our brain to see if we can find the data to overturn our hypothesis, so we should try to do this as intentionally as possible.
(我选A,这和我之前的选择也是相关的,我认为在临床实践中,我们的大脑倾向于证实我们的设想,所以我们必须尽可能有意识地强迫大脑去寻找数据来推翻我们的设想。)
栗占国教授:
我也选A, 还是有感觉,也在做相关的事情。
Anita Chong教授:
I also chose A.
( 我也选A。)
沈锋教授:
我也是A,因为我们大部分的工作都是围绕预测和模型。
孙凌云教授:
我也选A。
主持人肖飞教授总结
最后这道题,尽管现场所有专家的答案比较分散,但台上的嘉宾没有争议,都在有意识地建立和使用算法,然而建立临床的算法思维仍然需要长期的经验与知识积累。数据本身没有用,只有将其梳理、分析、翻译和应用,数据才有价值,是算法实现了数据从无价值到有价值的转化。
算法实际分两种,一种是医学生的模式,另一种是临床医生的模式,这是斯坦福大学的几个人工智能教授所说的。医学生模式是基于电脑的专家系统,这种模式下结论和路径都已知;临床医生的算法是基于机器学习,结论未知,需通过分析大量的数据而推导出结论,而且这些数据会不断更新,最后得出预测结果。
例如,一位孕妇站在我们面前,第二个因素是她患了RA,第三个因素是活动,第四个因素是焦虑,第五个因素是激素治疗,第六个因素是副作用高血糖,第七个因素是有经济条件……临床医生怎么治疗?临床医生只有获得这些信息之后才能做出判断,而不是单纯地遵循指南。
人工智能是什么?人工智能的定义是设计成模仿人类智能的算法和代码,其目的是将有价值的知识转化成有功能的知识。人工智能可以像人一样思考推理,经过海量数据的处理,人工智能实际上可以优于人类。我们现在宣扬“互联网+”医学,医生更容易获得知识,未来一定是“智能+”医学,让医生从优秀发展到卓越。现在我们提出来同病异治、异病同治的理念,本质上是指精准医学和共同规律。“两害相权取其轻,两利相权取其重”,这一理念也可以指导我们减药与加药。
图11列出了大约十几种药,这些都是数据库里拿出来的,用红色字体标注的NA都是指说明书里没有任何信息。比如说甲泼尼龙,说明书中没有任何肝损害的信息,但数据显示在真实世界其ALT升高的不良反应发生率将近5%。更令人吃惊的是,英夫利昔单抗在真实世界中的不良反应发生率为15%,但说明书上说不良反应率仅5%。
再比如单药对应的白细胞下降谱,这个谱(图12)单凭说明书是没办法完成的,只能靠大数据。
中国的风湿科医生在创造一个奇迹,例如,新疆的一位患者出现了不良反应,其远在北京协和医院的主诊医生就会收到警报信号,此时,医生通过数据平台可以看到这位患者采用了5种药物联合治疗,也能看到以单药甲氨蝶呤为基础的一系列不良反应谱。这5种药是由5个单药组成,可以形成30种撤药方案,这位患者由4种药联合过渡到3药联合、2药联合,最后过渡到1种药,人脑并不具备处理这类大数据的能力,但是采用马尔科夫模型就可以画出最安全的GPS撤药路线图(图13)。
图14是7616位类风湿关节炎患者三个月的转归β-distrbution图,从图中可以看到一部分患者复发,一部分变成了高活动度。我们怎么预测呢?目前没有办法,只能通过严密监测,例如像BeSt研究一样,每三个月评估一次,每次评定是否需要增药、减药或者换方案。
有本书的名字是《Deep Medicine》,作者是一位有名的医生,他说过,处理复杂数据的能力将成为区分优秀医生和一般医生的标准。所以,今天的医生要迎接这个挑战。
如何建立医学的天气预报?人类的共同起源保留了七大信号传导,包括症状、部位、器官、细胞、基因、蛋白到分子,这七大信号传导支撑着我们的生命,但也是它们引起了疾病,我们要做的是去寻找疾病的共同规律。(整理报道:刘艺红)